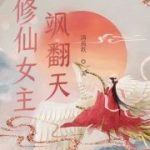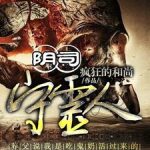第五百四十一章 中東(6)
“看來北非的天氣不錯嘛。”雅尼克熱情的歡迎從北非回來述職的隆美爾,不禁心中吐槽了一下這家夥明顯是借着述職的借口回來看望他老婆的,沒過幾天就是他老婆的生日。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隆美爾的愛情觀,可以用“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青年時代的隆美爾性格堅毅,腼腆內向,不吸煙,不飲烈酒,不近女色,始終過着嚴謹的斯巴達式的禁欲生活。1911年3月,隆美爾被送進但澤皇家軍官候補生學校進修,為期8個月,而他卻很少去體驗這座海濱城市燈紅酒綠的夜風景。
那時的但澤常常舉行軍官舞會,這些青年學生以及一些當地名門的女兒都會被邀請參加。在一場夏日的舞會中,隆美爾認識了一位名叫露西.莫林的17歲少女,并對之展開瘋狂的追求。
而露西一開始并不喜歡隆美爾,認為他過于嚴肅,和自己活潑的性格并不相稱,但當隆美爾戴起單片眼鏡惟妙惟肖地模仿其普魯士的軍官們時,她還是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兩人迅速陷入熱戀當中。
在軍校的學習生活中,隆美爾除去日常的學習、操練,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給露西寫情書上。這個習慣即使是在日後逐日吃緊的北非戰場也沒有改變。在北非,隆美爾每天都要給露西寫一封信,有時甚至是幾封。有的信工工整整,傾吐着閑暇時光的思緒,有的則寫在文件、日歷等部隊用品的背面,往往由他口述,副官執筆。在戰争結束後,露西保留着北非期間隆美爾給她寫的1000餘封信。這些信後來被美軍搜查走了。有趣的是,由于落款統統是“你的埃爾文”,所以這些信件并沒有被歸入隆美爾的材料中,而是另開了一個“埃爾文”的戶名。直到戰後很多年,這些信件才輾轉回到露西手中。
根據露西女伴的回憶,“隆美爾把露西寵得幾近嬌縱,他挂在嘴邊的話就是‘最親愛的露,有什麽要求你就說吧’,到後來,簡直把她寵得像一個潑婦。如果她不喜歡她的哪個女伴,其他人就必須一起排斥。”這樣看來,也不難理解當1944年隆美爾夫人和高斯的夫人發生口角後,隆美爾為何不留情面地把高斯趕了出去。
諾曼底登陸前,正好是露西的生日,因為前線天氣一直不好,隆美爾抓住這個機會返回德國為夫人慶祝生日了。
哪知道盟軍偏偏就選擇了這一天作為登陸日,戰場上戰機是稍縱即逝的,當隆美爾趕回戰場的時候,就算他是沙漠之狐也無力回天了。
彙報完北非的局勢後隆美爾提起了中東戰事。“殿下,進攻中東的猶大人集團軍……”
雅尼克邊在文件上簽名,邊随口問道。“他們怎麽啦?”
隆美爾猶豫了一下,才小心翼翼的開口道。“我聽說他們不接受對方的投降,甚至屠殺之前抓到的戰俘。”不接受投降進行屠殺和殺戰俘都是嚴重違反日內瓦有關條約的行為,從開戰到現在德軍從沒出現過這種事。
“哦?誰下的命令?”看着雅尼克這幅副波瀾不驚,淡定從容的樣子;隆美爾也猜出他已經知道了此事,不過還是如實回道。“是猶大人集團軍臨時司令。”
“你在想這是不是我下的命令?我是有這個想法,不過并沒有下達過命令。這個司令很有眼力見嘛,看來将來能成大事。”看着隆美爾而欲言又止的模樣,雅尼克繼續道。“有什麽好驚奇的,這些家夥各個都有當恐布分子的潛質,現在消滅一點是一點,難不成留着當後患。這也是我專門調遣猶大人進攻中東的原因。他們要在耶路撒冷建國,以後得經常跟阿拉柏人打交道,先讓他們練練手。”
談話間戈培爾博士來找雅尼克。“戈培爾博士,在報紙上登一下中東戰事,就說那些阿拉柏士兵各個骁勇善戰,戰鬥到最後一人寧死不屈,是值得敬佩的對手。”
聽得隆美爾目瞪口呆,那些阿拉柏士兵戰鬥力只能用渣渣來形容,簡直就是一觸即潰、不堪一擊;殿下卻說這些家夥骁勇善戰寧死不屈?
雅尼克笑笑道。“那些阿拉柏士兵都是英勇戰死的,誰敢說他們是投降後被處死的?就算傳出去誰信?”
“還有,我們将戰争中出現的難民送往美洲。美國人不是喜歡宣揚他們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麽,看他們收不收這些難民。一旦美國人拒絕接受,我們就大力抨擊美國人的虛僞。”
後世的全世界難民數量,那是有億級別,尤其是在中東地區,難民數量就有幾千萬。而大部分的難民,之所以成為難民,基本上都是因為戰争引起,在戰争下家園被破壞,財産散盡,最終淪為難民。
這些戰争大多跟美國有關,可以說是美國造成了這些民衆流離失所,理論上有責任幫助,接收難民;而另一方面,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享受世界利益。出于國際道義來說,美國也是有着最核心的義務,來接收難民的。
但事實正好相反,美國自始至終從來沒有接收難民,甚至非法移民也很難進入美國。他們奉行的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優先”。
美國只要利益,不要負擔。如果大批難民湧到美國,對美國來說,只有損害沒有利益。而且美國還擔心,難民的到來,會使得美國治安混亂,所以堅決不接收一個難民。他們只歡迎有錢,或者有才,或者有權的人到美國,移民美國,因為這對美國才是有利的。
而現在雅尼克準備把中東的難民統統送到美國去。雖然兩國宣戰,德國是不能親自送了,可還有不少中立國呢。
比如希臘。
剛好希臘最近跟德國談一筆軍火貿易,雅尼克便讓希臘幫個忙,給難民運輸船挂上希臘國旗;而希臘自然不敢得罪德國。